|
“上房瞭见王爱召”这首民歌已传唱了近一个世纪。全国很多地方把当地的民歌排成电影、电视剧来宣扬,大大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,从而成为旅游和投资的热点。反观我们,对这首民歌还没有充分利用。要想让它热起来,就得把它编造成故事,有人物,有情节,让人愿意看。这就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。 民国年间,后套大土地开发商王同春的女儿王友卿在伊盟达旗包租大量土地。社会传说,正是她和喇嘛的恋情才产生了这首民歌。王友卿是个有点污点的人物,前半生尚可,后半生不保晚节。如果把她原封不动写出来怕有不当。所以我以她为原型,塑造了王云青这一人物。而郑达所著《河套王》(百花文艺出版社)里,王友卿是以正面人物出现的。 王云青有其父的特点,为人豪爽,好助人为乐,一心想在达旗开发土地干一番事业,却事与愿违。正如奇朝鲁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,“王家的衰败,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”事业不成,婚姻失败,只有和喇嘛出走。还有社会最基层的几个女娃,如贾芬、谷三老婆等,那时候的农村妇女,不管是土匪还是官兵来了,首先就糟蹋妇女,就像新中国成立初期唱的那首妇女翻身歌“旧社会黑圪隆咚的枯井万丈深……妇女在最底层。”沙·木特喇嘛教的上层人物,虽然“七情六欲”皆有,他也爱他所爱的人,但他不会为女人而还俗当农民受重苦,只能是“两头”照顾。不觉间撞上了跟王爷争抢女人的险境,只有逃走。说到旗王爷,并不是一切都坏,他们也想做好本旗的事,让农牧民安居乐业。可是面对上面的军阀混战,一朝天子一道令,让他们无所适从。只有靠玩钱、玩女人,抽洋烟来消磨时日了。实在说,这是时代的悲剧。 文学创作的艺术真实是来源于生活真实。我在写拙作的过程中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,想再现民国年间黄河沿岸的民情民风。诸如市面上流通的货币、粮食的价格,归化城都统署给各地下达剪辫子的任务,达旗王府把士兵吃的油肉、酸菜、山药都摊派给农户等。还有“走西口”来的汉人,都想当随旗蒙古人,给旗王爷送块砖茶,这份礼也够贵重了,穷人家是承受不了的。所有这些,都是当时真实情况。 对于拙作的成败,奇朝鲁会长在序言中和潘洁先生在“评介”中均作了肯定,这倒使我诚惶诚恐。败笔之处潘先生也点到,如王云青出家显得突兀和匆忙。现在想来,应再加几千字,如王府抓沙喇嘛,他逃到了王家,王云青把他藏起来,两人缠缠绵绵呆上几天,商量出走的路线及遇到的麻烦,然后再逃走。这样便无仓促之感了。 在研究会举办的书评会上,专家学者对拙作讲了很好的意见,既做了肯定,也指出了不足,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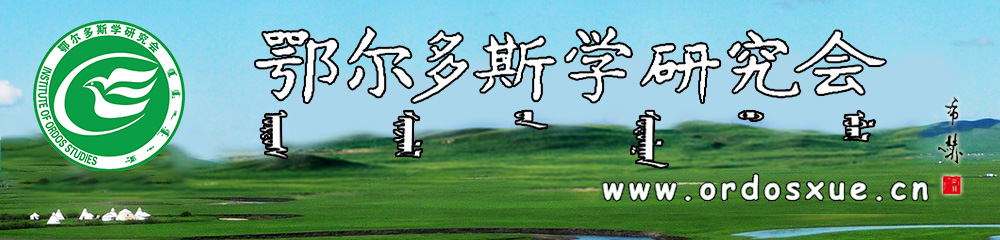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
蒙公网安备15060302000300